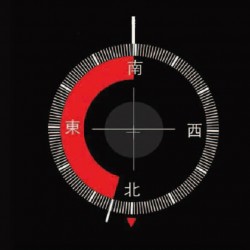「我的日記就在我的工作、我的音樂中」─ 托米.佩爾松眼中的魏因貝格
古典音樂台

音樂 Weinberg:Sonata for violin & piano No.4, Op.39, Mvt.2 Allegro ma non troppo - Adagio primo
(試譯自DSCH Journal No.49) 漢妮.范.德.赫路普 / 文
DECCA CHU / 編譯
多年來,魏因貝格(1919-1996)一直是最被忽略的蘇聯作曲家之一。諸多因素之一是他過著隱居的生活,加上他不熱衷於推廣自己的作品。魏因貝格是個低調的人,而他的作曲才華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籠罩在蕭士塔高維契的陰影之下,雖然後者非常欣賞這位同事和朋友。過去的幾年,魏因貝格這個名字才終於開始較頻繁的出現在音樂會曲目中。
DSCH Journal很榮幸能與促成魏因貝格音樂復興的背後,一位關鍵但低調的人物見面並討論。他與魏因貝格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一直不遺餘力的在世界各地推廣魏因貝格音樂的能見度。我們與托米.佩爾松的這則訪問是2017年在德國戈里施的蕭士塔高維契音樂節後進行的。托米.佩爾松出生於1945年,1971年起在瑞典哥特堡的地方法院擔任法官,審理各式各樣的民事和刑事案件,2010年退休。儘管蕭士塔高維契在他心中佔有特別的一席之地,但他對幾乎所有的俄國音樂都充滿熱愛。後來他從一本關於俄國音樂的書中認識了魏因貝格, 從那之後魏因貝格的音樂也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DSCH:魏因貝格的音樂對你有何意義?你最初是怎麼接觸到他的音樂的?
TP:對我來說,魏因貝格的音樂有一種罕見的力量,能夠以一種無所不包的、純粹的、人性化的聲音傳達出各種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一切都從1972年開始。我非常喜歡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總是盡可能的閱讀任何關於他的資料,也買了很多他的唱片。我很高興能在如此浩瀚的
音樂世界中發現這位作曲家。1972年,包里斯.舒瓦茲(Boris Schwarz)的《蘇聯的音樂與音樂生活,1917-1970》出版,這本書現在滿有名的,而我就是從書中認識范因貝格(那時的拼法,Vainberg)。我從沒聽過名字,也沒聽過他的音樂。我從書中得知他是一位很有天份的作曲家,寫了非常多曲子,但在西方世界比較少人知道。透過舒瓦茲的書,我了解到魏因貝格或許是能夠繼承蕭士塔高維契交響樂衣缽的作曲家之一,於是我試著找些他的錄音來聽。
DSCH:在瑞典?
TP:那時哥特堡有一間很棒的唱片行。我認識經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對古典音樂瞭若指掌。他幫我弄到一本1975年版的Melodiya全部唱片目錄,非常厚。不過那裡面列出的魏因貝格唱片我一張都沒買到,包括題獻給孔德拉辛(Kirill Kondrashin),並由他指揮錄音的第5號交響曲,第1號長笛協奏曲,還有第4和第5號鋼琴奏鳴曲。
DSCH:沒有《兒童的音樂筆記》 或他的歌曲嗎?
TP:沒有,你說的這些作品都沒在目錄中,只有幾首他的管弦樂,室內樂,和器樂曲。我在英國有找到一些二手LP,但都太貴了。所以又多花了一些時間。1976年12月,就在聖誕節前不久,EMI發行了一張Melodiya的三首小號協奏曲錄音,其中一首是魏因貝格於1966到67年間寫的,由齊烏拉伊提斯(Algis Zuraitis)指揮波修瓦劇院院團,著名的多克西哲(TimofeyDokshitser)擔任獨奏,魏因貝格這首協奏曲就是題獻給他的。我馬上郵購這張LP,然後被這首協奏曲深深著迷。
DSCH:很有趣的音樂!
TP:確實很有趣,但也包含一些陰暗的色彩。裡面引用了孟德爾頌的《結婚進行曲》,還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金雞》。第一樂章聽起來鬧哄哄的,我認為這可能為蕭士塔高維契寫他的第15號交響曲第一樂章時帶來一些靈感。在我看來,這兩個樂章有著同樣興奮昂揚的氣氛。1977年四月,我太太安-克莉斯汀和我去巴黎,在那裡發現一間超棒的唱片行,裡面有成千上萬張LP。
DSCH:你記得找到什麼特別的錄音嗎?
TP:有,我找到兩張Le Chant du Monde發行的Melodiya錄音。其中一張有第4號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孔德拉辛指揮莫斯科愛樂,獨奏者柯岡(Leonid Kogan)。另一張是當時還很年輕的布魯希洛斯斯基(Alexander Brussilovsky)演奏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魏因貝格的第2號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那是作曲家題獻給菲赫騰戈爾茲(Mikhail Fikhtengolts)的,也正是我們今年(2017)在戈爾施的音樂節聽到的那首迷人作品。對我而言,第4號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都非常具有溝通性,一如我聽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時所經歷的。當然,我不是什麼都懂,不過我被他這種音樂語言深深震撼。我非常高興發現了這位「新」作曲家。
DSCH:你的下一步是?
TP:我繼續試著尋覓更多魏因貝格作品的錄音,不過都找不到。後來我聯繫了瑞典廣播電台:那時他們的第二頻道有一個每週日下午三點播出的節目,叫作「新時刻」,聽眾可以指定音樂請電台播放,比如某首交響曲的某個樂章。我在那之前就有寫去過,請電台播放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這次我請他們播放魏因貝格的作品。事前我有跟一位在瑞典廣播電台留聲檔案處工作的人確認過,知道他們有一些魏因貝格作品的LP,大部分是Melodiya的錄音,當中有些是由美國的Westminster發行。我請該頻道從這些LP中選播幾首作品,例如第5號交響曲。後來,這個節目的負責人注意到了,他們寫信給我,說他們發現這位作曲家值得引人關注,並謝謝我提出這個請求:「這為聽眾們增大了聆聽的廣度。」
1980年底,我太太和我去列寧格列旅行一週。我帶著一張從Melodiya目錄上抄下來的清單,到涅瓦大街上那間很大的Melodiya唱片行,不過店員聳聳肩:「魏因貝格?不,不,從來沒聽過他。」我很失望,只好再問:「那你們有蕭士塔高維契作品的LP嗎?」他們只有一套兩張的LP,列寧格勒(第7號)交響曲。我跟我們的瑞典嚮導說我有多失望,來到了蕭士塔高維契出生的城市,卻兩手空空的回家。她說:「我可能有個辦法 -- 我有個朋友跟她父親就住在這裡,他們是瑞典男高音蓋達(Nicolai Gedda)的大樂迷。或許你們可以交換LP,蓋達交換魏因貝格。」隔天早上,也是我們那次旅行的最後一天,我們跟這位叫作瑪麗亞的年輕女子見了面,並交換了地址。我們會分別從瑞典和俄國幫對方尋找想要的LP。她幫我弄到幾張魏因貝格音樂的LP,像是第12號交響曲,這首是他於1975到76年間為紀念蕭士塔高維契而寫的,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這份錄音是1982年六月,費多雪耶夫(Vladimir Fedoseyev)指揮中央廣播與電視管弦樂團的現場錄音。事實上,當時很多俄國作曲家都有寫曲子紀念蕭士塔高維契。
另外,我還收到一張魏因貝格的第1號無伴奏中提琴奏鳴曲,由杜齊寧(Fyodor Druzhinin)演奏,該曲正是題獻給他的。唱片的另一面是魏因貝格一位朋友,弗利德(Grigory Frid)的中提琴奏鳴曲。我覺得弗利德在西方應該值得更大的知名度 -- 他的作品太少被演奏了。瑪麗亞還幫我弄到幾張二手LP,包括孔德拉辛指揮的第5號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我已經有了),以及現在非常有名的摩爾多瓦狂想曲!後者是改編成給小提琴和鋼琴演奏的版本。
我的列寧格勒朋友還幫我要到魏因貝格的住址。我聽過他的音樂,一遍又一遍的讚賞不已,但這似乎還不夠。我發現他的生日是12月8號,於是我想 -- 何不寫信給他?我還記得蕭士塔高維契是在8月9號過世的,隔天早上我才從瑞典廣播電台上聽到消息。那天我真是極度沮喪,後來還哭了,我覺得這個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作曲家。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我對魏因貝格不應該犯跟對蕭士塔高維契一樣的錯誤,沒有寫信告訴他,他的音樂對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我當時只知道魏因貝格很欣賞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但以為他們只是互相認識,偶有聯繫而已,還不曉得他們深厚的友誼。
我買了三張蕭士塔高維契的LP,其中一張是第13號交響曲:我從資料中得知魏因貝格是少數這首交響曲開始彩排前就聽過的人之一。他是跟羅斯托波維契(Mstislav Rostropovich),維許涅夫斯卡雅(Galina Vishnevskaya),孔德拉辛等人一起在蕭士塔高維契家聽的,因此我想他應該會喜歡這首交響曲的唱片, 尤其考慮到他是猶太人,而他就是在納粹德國入侵時逃離波蘭的。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魏因貝格,祝他生日快樂。我只用英文寫了短短幾行,告訴他我很喜歡他的音樂,他的音樂對我意義重大,並祝他一切安好等等。
DSCH:這是哪一年的事?
TP:1984年十二月。兩週後我收到一封魏因貝格拍來的電報,從斯拉夫字母音譯過來的。他寫得非常客氣,就我送給他的LP和生日祝福表達感謝,並以他對我最真摯的祝福作為回報。
DSCH:我猜你一定還留著!
TP:噢是的,當然!不過,我怕打擾到他,所以過了好幾個月都沒回覆。我只是想讓他知道在這個叫作瑞典的奇怪北方國家,有個人非常喜歡他的音樂,我希望這對他來說是有些意義的。幾個月後我才又寫了一封信給魏因貝格,告訴他關於我朋友從列寧格勒寄來的一些他的LP,從那時起,每年他的生日我都會寫信祝賀。1988年,我太太和我去烏茲別克旅行。我知道戰爭期間魏因貝格曾在那邊待過。
DSCH:在塔什干‧‧‧
TP:是的,他為了躲避納粹逃亡到該地。事實上,1939年到1941年間,他原本是在明斯克,直到1941年六月納粹往蘇聯進攻,他只好逃跑;雖然,根據他身上的文件,他是不能離開明斯克的,這點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的作曲家同事克魯莫夫(Aleksey Klumov)幫忙弄到偽造的文件,他才得以搭上離開明斯克的火車,前往塔什干。那段漫長的路途大概需要兩週時間。
DSCH:他也在那邊結了婚?
TP:那是後來的事。1942年,他跟 娜塔莉亞.沃芙西-米霍埃茲(Nataliya Vovsi-Mikhoels)結婚,她是偉大的猶太演員和莫斯科劇院負責人所羅門.米霍埃茲(Solomon Mikhoels)的女兒。
DSCH:讓我們回到你1988年的旅行。
TP:我們從赫爾辛基搭火車出發,途經列寧格列到達莫斯科,再從莫斯科飛到塔什干,在那裡停留四天。其中一天晚上我們去歌劇院,上演的是葛拉祖諾夫的芭蕾舞劇《萊蒙達》。我知道戰爭期間魏因貝格曾在這間歌劇院擔任合唱團的聲樂指導,光想到這一點,就讓我在踏進劇院時興起一股特別的感覺。接著我們去了撒馬爾罕,我在那裡病得很嚴重,我們瑞典人稱之為red fever(地方性斑疹傷寒)。從撒馬爾罕飛回莫斯科後,我們在宇宙酒店住了一晚,一個奇怪的地方。儘管我燒得很厲害,我還是在那個十月的夜晚首次撥了電話給魏因貝格。這要感謝一位跟我們同團,在莫斯科教過多年瑞典語的俄文教授,她設法幫我找到魏因貝格的電話號碼。電話是魏因貝格的女兒安娜(Anna Weinberg)接的 -- 她出生於1971年 -- 我們開心的聊了20幾分鐘,後來她說「噢!你何不乾脆過來一趟!」不過因為我的病情嚴重,沒能成行。我對俄文一竅不通,所以之前給魏因貝格的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我沒想過用德文寫,覺得那樣可能不是很恰當,因為他的雙親和妹妹都死在納粹手中,而他也被迫離開祖國波蘭。感謝老天,安娜的英文說、寫都好極了。後來她以語言學家的身分在莫斯科大學進修英文。可以說安娜擔任了魏因貝格和我之間的「媒介」角色,並幫忙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例如「你現在在寫什麼曲子?」或「你好嗎?」等等。我的信都寫得很簡單,卻都得到非常溫暖的回覆!
DSCH:你有跟他討論他的作品嗎?
TP:我只有問他最近的創作計畫。要到1995年,我才拿到他那數量龐大的全部作品清單,在那之前很難,只能從Melodiya的唱片解說中找到一點點資料,跟圖書館和百科全書中殘缺不全的列表。當時我只知道11首弦樂四重奏,9首交響曲和一些其他作品,主要是室內樂。既然有了電話號碼,我開始打電話給魏因貝格,儘管1988年從瑞典打到俄國的電話費是非常昂貴的;因此我都會盡量縮短通話時間在大約六、七分鐘。不過,無論花費多少都值得,因為我們可以聽到彼此的聲音。我記得有一次打電話向魏因貝格祝壽(用俄文說這個我還辦得到),並問他過得如何,他回答說:「我正在工作。」很多年後我才從他的遺孀奧爾嘉.拉赫爾斯卡雅(Olga Rakhalskaya)那裡知道,他一天24小時都在工作。她說,他甚至連睡覺的時候,手指都會像在彈琴一樣動個不停。音樂和工作佔據了他所有的時間。
DSCH:後來你就發現他生病了?
TP:那是後來才知道的。1990年,我到列寧格勒去拜訪幫我找魏因貝格唱片的朋友,原本只打算待個幾天。就在準備要離開前,我作了一件蠢事,我寫信問魏因貝格是否可能從莫斯科來列寧格勒跟我碰面。那時俄國郵政的效率不彰,以至於我離開列寧格勒時,信還沒送到莫斯科。無論如何,魏因貝格說他沒法過來。然後他跟他的家人邀請我去拜訪他們。這就令我難以想像了 -- 我去那邊要作什麼,我不是音樂家!後來我的身體出了狀況。1991年,我的背斷掉了,整個暑假(五個禮拜)都只能躺在床上。我動彈不得,八月間試著返回工作時,只撐了兩天就回家了。後來,那年的剩餘日子我都無法工作,只能靜養,然後1992年一月底動手術,手術完又花了很長的時間復健,因為我很多肌肉都失去作用了。那段時間非常難熬,一直到四月底我才開始做25%的工作,儘管六月時我就回到全職。那年我甚至想都不敢想要出國。1993年,法院的工作非常忙碌 -- 我每週的工作時數從沒低於55到60小時。
DSCH:後來呢?
TP:1993年初,安娜在電話中跟我說:「你至少可以來參加一下我父親的75歲生日吧!」(那會在1994年十二月)當然,我無法拒絕,我一定要去!那時我就知道他的身體不是很好,儘管詳細狀況是一無所知。1993年夏天,我們的列寧格勒朋友瑪麗亞和她兒子來瑞典找我們,待了五週。他們快要回去時,我跟她說:「請妳幫個忙,我們來打電話給魏因貝格,妳會說俄文,問看看他的狀況到底如何。」安娜說她父親已經罹患嚴重的克隆氏症多年,加上1992年的秋天,他在家中跌倒導致臀部破裂,不得不臥病在床。她還跟瑪麗亞說魏因貝格亟需治病的藥物,但因為他已經無法作曲,沒有收入的來源,而這種藥在俄國又極度昂貴,只能用美元買。我有一個醫師朋友,便請她幫忙開治療克隆氏症藥物的處方。她開完,我到藥局買了這昂貴的藥後,就交由瑪麗亞帶回列寧格勒,她說她會請一個常去莫斯科的朋友拿去魏因貝格在斯圖登切斯卡亞街的寓所。不久後,安娜就跟我說她父親的病情有因為我寄去的藥而好轉一些,這是1993年秋天的事。1994年五月,安娜再次跟我說,這些藥讓她父親的健康狀況又更進步了,讓他能夠短暫下床,用輪椅坐在鋼琴前完成一首新的交響曲,也就是第22號交響曲;不過只有鋼琴稿,他還無法為其配器。
1994年對魏因貝格來說是重要的一年。一月間,英國唱片公司Olympia開始發行一系列魏因貝格的CD。第一片CD收錄了他的第6和第10號交響曲,第6號交響曲是獻給他最年長的女兒維多利亞,她當時住在台拉維夫;而第10號交響曲是題獻給巴夏(Rudolf Barshai)的。我馬上聯繫Olympia,跟他們說我和魏因貝格有在聯絡,他們覺得太棒了。CD一出,我就跟寫CD解說冊的佩爾.史坎斯(Per Skans)聯繫;我們是1988年認識的。後來,那17張魏因貝格CD的解說冊幾乎都是他寫的,只有一張不是。在我繼續說之前,我想提一下關於喬治亞指揮家喀奇澤(Jansug Kakhidze)的事。1988年,他受邀到哥特堡歌劇院指揮四場蕭士塔高維契的歌劇《卡特琳納.伊茲梅洛娃》。有一天,我在一間常去的唱片行看到一個海報上的人:喀奇澤,他在那裡買了一條在他的家鄉提比里斯可能買不到的線。他是喬治亞國家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我沒弄錯的話,康切利(Giya Kancheli)所有的交響曲都是由他首演的,其中幾首還是題獻給他的。那時距離店家關門只剩20分鐘,於是我直接走向他,用英文問:「不好意思,請問你是不是喀奇澤?」「我是。」我跟他說我非常喜歡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他指揮的四場《卡特琳納.伊茲梅洛娃》我買了其中三場的票。我也順便向他提到我跟蕭士塔高維契的好友魏因貝格有聯絡,他說他聽過這個名字。後來,我邀他在其中一天晚上來我家聊天並共進晚餐。我開車到旅館接他,那晚很愉快。隔天,我撥電話給佩爾.史坎斯(Per Skans) -- 當時他還是斯德哥爾摩瑞典廣播電台的製作人 -- 因為我知道他多年來一直對蘇聯的音樂很有研究,而我自己當然也是很有興趣。佩爾說:「你說什麼!喀奇澤現在人在哥特堡?」他不曉得這位指揮家來指揮蕭士塔高維契的歌劇。可惜,佩爾沒辦法去看其中任何一場演出,但我給了他喀奇澤下榻飯店的電話號碼。佩爾打給他,他們聊了很多。原來,他們1975或76年就在提比里斯見過面了,那時佩爾和另兩位同事一起到蘇聯旅行。佩爾很喜歡喬治亞,講到那次的造訪都滿腔熱血。
話說回來,1994年,我終於決定答應邀請前往莫斯科,跟魏因貝格和他的家人同住五天。就在同時,Olympia的頭兩張魏因貝格的CD剛出版不久,後面的兩張也即將發行,我前往莫斯科的前幾天正好收到。於是我帶著好幾張CD去給魏因貝格;Olympia的賈姬.康波(Jackie Campbell)跟我說如果他們直接把CD寄給魏因貝格,會害他必須付一大筆關稅,而他負擔不起那些錢。於是我們決定,由我帶幾份最新發行的兩張CD(Olympia的魏因貝格系列第3、4集)過去,其中一張包括第12號弦樂四重奏,以及,更重要的,1963年由魏因貝格本人彈奏,跟包羅定四重奏合作的鋼琴五重奏錄音。
1994年12月7日,我來到魏因貝格家。開門的是安娜,她歡迎我,說:「爸爸在他的書房睡覺。待會你就會看到他了。」那時奧爾嘉(魏因貝格的第二任妻子)還在教堂幫助貧窮老人,比較晚回家。他們非常友善的接待我,讓我很感動。抵達後一陣子 ,我就獲邀進到魏因貝格的書房跟他打招呼。我帶著慶祝他75歲生日的禮物:一個大花瓶,裡面盛著一大束花。安娜和奧爾嘉提醒我別在魏因貝格的房間待超過30分鐘,他必須休息。魏因貝格的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差,他躺在床上,瘦骨嶙峋,留著鬍子,但眼睛顯得年輕而有朝氣。說來難過,他的手抖個不停,無法控制,增加了他作曲的難度。他的身邊有一個電話,隔壁房間也有一個。「當爸爸需要什麼的時候,他就把電話拿起來再放回去。」安娜說道。他們在隔壁聽到「噗拎」聲,就知道他需要幫忙了。
我發現很難問魏因貝格像是「你有被這個國家迫害嗎?」這樣的問題,因為我知道對他來說,他的生命是在被允許進入蘇聯的時候獲救的。很多從波蘭往東逃亡的猶太人都被送回去給納粹,或者被直接送進古拉格(蘇聯的勞改營)。我也曉得他將第1號交響曲獻給紅軍,那首是1943年二月在塔什干完成的。那年稍晚,他設法將手稿寄給蕭士塔高維契。沒有定論那份譜究竟是誰送到莫斯科的,只知道不是他的作曲家同事兼蕭士塔高維契的學生列維廷(Yuri Levitin),就是他的岳父米霍埃茲。1943年初, 米霍埃茲從塔什干前往莫斯科。那年五月,他跟詩人菲費( Itsik Fefer )作為蘇聯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的代表,前往美國和英國進行為期七個月的訪問,為蘇聯的戰事尋求募款和政治支持。 對了,你知道魏因貝格的第1號交響曲作品編號跟蕭士塔高維契的第1號交響曲一樣都是Op. 10嗎?蕭士塔高維契之前就聽過魏因貝格這個名字,也想更了解這位作曲家。他很喜歡那首交響曲,並安排魏因貝格和他太太(米霍埃茲的女兒)在莫斯科定居下來;那是1943年八月的事,他跟魏因貝格第一次見面則是在該年十月。我沒記錯的話,魏因貝格的大女兒維多利亞是1943年十月出生的,也就是說在他們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中,他太太就有身孕了,或許那就是他們決定去莫斯科的原因之一,那裡比較安全。後來我才知道,魏因貝格在塔什干的時候很常生重病(腸胃方面)。奧爾嘉跟我說,有可能他就是在那裡被傳染克隆氏症的。另一方面,魏因貝格年輕時還曾因結核菌感染背部,造成他經年累月的痛苦。背痛、臀部破裂、克隆氏症,加上被音樂界所忽視 -- 1994年的他情況是如此悲慘。
無論如何,在那裡的五天我們聊了很多,關於他的作品或其他話題。舉例來說,我問他「如果讓只能挑一部作品,哪一首是你認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他不加思索的回答道:「《乘客》,那部歌劇。」他說,雖然那是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不過還沒有機會上演。我得到最棒的招待和最溫暖的情誼,儘管因為魏因貝格的病情,他已經兩年完全沒有收入了。他們真的都非常的和善。我們天南地北的聊,奧爾嘉回答我所有的問題。她不會英文,但跟維多利亞一樣有學過法文,所以我們用的是「國際語言」:一些法文跟幾個我知道的俄文單字,加上大量的手語。奧爾嘉給我看了魏因貝格的所有家庭照,包括她的父母親等等。如果安娜和奧爾嘉不曉得我問題的答案,他們會問魏因貝格。我們還一起聽了所有我帶去的CD。
DSCH:他喜歡嗎?
TP:噢是的,那真是很棒的時光,尤其是我們一起聽他本人彈鋼琴的鋼琴五重奏錄音時。那首是1944年寫的,對我而言是深具吸引力的曲子,裡面似乎隱含著大量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
我還要提另一件事。儘管他寫了數量那麼龐大的曲子,還曾是莫斯科音樂圈的重要人物(特別是1960和70年代,1980年代稍減),在他75歲生日的這一天,莫斯科連一場演出他作品的音樂會也沒有,如此備受冷落當然令他難過。不過是有滿多人打電話向他祝壽,也證明還是大家沒有完全遺忘這位作曲家。那天下午,年輕的指揮家維德尼可夫(Alexander Vedernikov)--幾年後他將成為波修瓦劇院的總監 -- 來到魏因貝格的寓所。他帶著一捲錄音帶作為禮物,裡面是魏因貝格最新完成的作品,第4號室內交響曲(1992)的現場錄音;1994年十一月,維德尼可夫在莫斯科的秋天音樂節中指揮這部作品的首演。我們就一起聽了那個錄音,聽的時候,魏因貝格躺在床上仔細對照樂譜,非常有意思。那時我還沒聽過(也不曉得有)這首曲子,但我馬上被這迷人且發自內心的音樂深深震撼。音樂的最尾聲處聽來就像生命正在流逝。我想,他寫這首作品時,覺得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向終點了。12月8日下午五點左右,一位莫斯科波蘭大使館的官員來訪,頒發波蘭傑出文化服務獎給魏因貝格。他們單獨在他房間裡就波蘭的文化事務聊了一個多小時。那天稍晚,奧爾嘉、安娜、我, 梅德維傑夫(Alexander Medvedev,魏因貝格其中四部歌劇的作詞者)和他的妻子奧爾嘉,以及妮基提娜(Lyudmila Nikitina,她曾在1972年就魏因貝格的第1到第10號交響曲寫過一篇論文)為慶祝作曲家的生日,一同享用了一頓很棒的晚餐。可惜的是,魏因貝格的健康狀況太差,無法離開床上。梅德維傑夫和妮基提娜都是非常和善的人,兩人都提供我大量關於魏因貝格作品的資訊。伊琳娜.安東諾芙娜.蕭士塔高維契先前就有跟奧爾嘉說她無法在12月8日那天到場,隔天才造訪並向魏因貝格祝壽。作為蕭士塔高維契音樂的愛好者,我當然非常高興能跟她見面。
12月11日早上,就在我準備啟程回家前,安娜跟我說:「爸爸有東西要給你。」幾分鐘後,我們走進他的房間,他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新一部作品,第22號交響曲的前幾個小節,在那之上,還寫了一段親切的話給我。不過他把「1994年12月11日」寫成「1994年8月11日」了。那是我所擁有最珍貴的東西!
DSCH:你跟我說過,魏因貝格跟大使館的人用流利的波蘭語講話,即使已經那麼多年沒講了-- 真是驚人!
TP:奧爾嘉跟我說,他非常開心能說波蘭語,我也聽別人說他的波蘭語講得非常好。他從來沒忘記關於波蘭的記憶,家裡還有大量的波蘭文學。1953年二月魏因貝格被逮捕時,他問審訊人員他的罪名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加上意圖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共和國。魏因貝格說,真有那麼一回事的話,那也應該是波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因為他連一個意第緒字母都看不懂,家裡倒是有2000本波蘭文的書!在我離開莫斯科前,我告訴魏因貝格,Olympia已經跟蘇格蘭鋼琴家麥克拉赫蘭(Murray McLachlan )簽約,要用兩張CD錄下他的六首鋼琴奏鳴曲。幾年前,麥克拉赫蘭在大不列顛的一家譜店買到前三首奏鳴曲的譜,不過遍尋不著另外三首。魏因貝格說我可以問看看維多利亞,但我聯絡上她後,她說她沒有那些譜。最後,那些譜才在莫斯科的作曲家協會被找到,我們從那邊訂了幾份。原本的計畫是要在英國錄音,不過當時,1995年,Olympia出現了重大的財務問題,因此無法為該計畫提供資金。與此同時,魏因貝格病得更重了。我向Olympia提出建議,與其在英國,不如在哥特堡錄音,我可以承擔所有花費。我有個好友叫史溫生(Tomas Svensson),他在哥特堡有一間音響店,之前製作過一些很棒的錄音,他說他可以負責錄音工程的部分。另外,他跟一位鋼琴家朋友談過了,赫德瓦爾(Ingemar Hedvall)願意擔任這個錄音計畫製作人的工作。Olympia馬上就同意了。接著,我去哥特堡音樂與戲劇高中,一所新設在一棟新建築物的學校。他們的室內音樂廳音響效果很不錯,我跟負責管理的人協議租下一個週末,費用大約是幾千克朗(大約等於幾百歐元)。Olympia的經理康波住在我們家,她和我一起負擔麥克拉赫蘭的機票和旅館費用。所有人在1996年11月7日到齊,那個週末,我們錄了六首鋼琴奏鳴曲及作品34《21首簡易鋼琴小品》中的17首。史溫生和赫德瓦爾都是義務幫忙。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不錄,沒有其他人會錄這些作品。這就是Olympia一系列魏因貝格CD中我所「負責」的第一批。11月10日星期天,麥克拉赫蘭彈了一場獨奏會,曲目包含魏因貝格的第2號鋼琴奏鳴曲及另外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前者想必是西方首演。這場音樂會是應一個音樂協會的請託辦的,地點是在賽勒,約在哥特堡南方2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這首不知名俄國作曲家的奏鳴曲深受聽眾的喜愛!
那場音樂會的前幾天,哥特堡弦樂四重奏的團員跟我說他們有興趣錄幾首魏因貝格的弦樂四重奏。 出席麥 克拉赫蘭那場音樂會的聽眾中,有一位叫做史維隆(Thord Svedlund),他是哥特堡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也是指揮家,他原本就對魏因貝格的音樂相當熟悉。從那時起,我們成了摯友,一起推廣和錄製魏因貝格的音樂。史維隆是魏因貝格的強烈信徒,沒有指揮家比他錄過更多魏因貝格的管弦樂作品,其中五張CD由Chandos發行,兩張由Olympia發行。可惜,魏因貝格於1996年二月過世,不過至少他生前就知道我們錄製他鋼琴奏鳴曲的計畫了,雖然是在瑞典而不是英國。
魏因貝格過世後,我跟還在瑞典廣播電台工作的佩爾.史坎斯說「你一定要製作一個魏因貝格的節目。他才剛過世,我們得要在他被徹底遺忘前作些什麼。」他喜歡這個想法,不過卻說「你何不來自己作呢?」,我婉拒了。佩爾說「新時刻」的節目製作人,作曲家拉貝(Folke Rabe),應該會有興趣,但是我聯絡到他時,他也建議我自己作。我沒有相關經驗,所以起初還是拒絕此提議,不過最後還是同意了。拉貝建議我去找哥特堡瑞典廣播電台音樂部門的製作人,這位先生對製作這個節目的想法很感興趣。五月底,我已經擬好草稿,並從魏因貝格的作品中選出六段音樂。我將這個30分鐘長的節目定名為「莫伊西.范因貝格或米茲斯洛夫.魏因貝格 -- 蕭士塔高維契一位作曲家摯友的一生 」,我試著在節目中為他的人生和作品勾勒出一個樣貌。節目在1996年6月7日播出,五天後重播。如前所述,我跟哥特堡弦樂四重奏一直保有聯繫,他們當中有三位團員都是哥特堡交響樂團的團員,中提琴手則是哥特堡歌劇院的樂手。我跟他們說魏因貝格一共寫了17首弦樂重奏,沒有任何一首有錄過音,不知他們是否有興趣錄個幾首。Olympia跟我們決定錄三首四重奏,剛好可以收進一張CD。我們詢問奧爾嘉應該選哪三首來錄,她選了第1、第10(題獻給奧爾嘉)和第17號四重奏,在魏因貝格超過60年的創作生涯中,這三首的創作年代就跨越將近50年。跟上次一樣,CD的支出由我搞定,1997年春天在哥特堡東方約60公里的一個教堂進行錄音。跟史威隆認識後,我們也決定設法錄一些魏因貝格的管弦樂作品,由他擔任指揮。但在那之前,得先拿到總譜、分譜,然後找到一個樂團!托德(史威隆)指揮過幾個瑞典樂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後,他終於和于默奧交響樂團簽訂合同,預計錄製四首魏因貝格的作品:第1、2、4號室內交響曲,以及創作於1945-46年的第2號交響曲。在奧爾嘉和安娜的協助下,我們與莫斯科的作曲家協會取得聯繫,試著從那裡拿到錄音所需的資料,同時,在一位佩爾所認識定居在斯德哥爾摩的俄國人協助下,從作曲家協會和作曲家之家那邊買到總譜和分譜。不過,三首室內交響曲沒有分譜,後來是靠安娜用手抄寫的方式把分譜寫出來,再花錢找到一位朋友印成最終版。我們有個期限,于默奧的團員必須在那之前拿到分譜才有足夠的時間練習。不過因為抄寫分譜的工程浩大,還是有些耽擱。不過,最後我和托德、製作人和錄音工程師仍能照計畫中的日期抵達于默奧,在史特倫貝克民眾高等學校的大廳架設好錄音設備。1998年五月,我們在此錄了第1、2、4號室內交響曲。當時我們還不曉得時間總長多少,會需要一張或兩張CD。結果錄音後製完成後,發現還可以容納一些音樂進一張CD,於是我們決定再錄一首,第2號交響曲,1998年10月一樣在于默奧錄製。我們很滿意,覺得自己達成一些重要的事情 --魏因貝格四首管弦樂作品的「世界首錄」,後來這些錄音分別於1998和1999年發行,是為Olympia魏因貝格系列的第15和16集。
我跟Olympia從1994年起密切合作,我們一起探查現存的魏因貝格錄音,例如俄羅斯國家廣播電台裡的檔案。我大概算是Olympia在魏因貝格音樂方面的顧問,而佩爾則為新出版的CD撰寫內冊解說,儘管他也只有書本和百科上的資料。魏因貝格還在世時,我當然可以就個別作品詢問相關細節並記下任何他能提供的答案,而他過世後,安娜和奧爾嘉也提供不少資訊,例如曲子的創作日期、地點及被題獻者。
魏因貝格過世後,奧爾嘉和安娜的景況不是很好,因為她們沒有收入。奧爾嘉把她大部分時間都奉獻在教堂,幫助老人和病人,她可說是「教堂護士」。安娜則繼續忙她的大學學業,但有時也會擔任翻譯員打工,或在美國大使館教人俄語,偶爾還有些私人學生。1994年我去莫斯科拜訪時得知奧爾嘉的身體不好,她有支氣管炎和氣喘的毛病,常常需要吃藥。幸好,托德的太太是醫師,她幫我開藥,我再連同其他奧爾嘉和安娜需要的東西一起寄去給她們。我很樂意為她們作點事情,因為他們真的待我如家人,而我唯一做過的,就是欣賞這位作曲家的音樂,告訴他這對我有多大的意義。
後來我跟佩爾一起設法幫奧爾嘉在西方找出版商,把魏因貝格的作品推廣給更廣大的群眾。佩爾跟鋼琴家涅姆佐夫(Jascha Nemtsov)聯繫過,我猜就是他說漢堡的Peermusic出版社有可能會對出版魏因貝格的作品有興趣。蘇聯時代,魏因貝格的一些重要作品是由漢堡的Sikorski出版社出版,且直到今日還保有版權。然而,重要的是找到一個有興趣盡可能多出版魏因貝格大量作品,使其更為廣為人知和演出的出版商。當時,掌管Peermusic古典部門的是弗蘭德(Reinhard Flender),我們一起跟奧爾嘉談,最後她決定跟他們以一首一首的方式簽訂合約。
蘇聯時代,魏因貝格作品的版稅都是支付給作曲家協會的,魏因貝格本人幾乎拿不到什麼錢。不過他身為作曲家還是有些特權,像是有個好公寓可住,可以進到某些特殊商店,還有鄉間小屋可享受假期。我待在魏因貝格家的最後一天,我答應他會盡我所能的推廣他的音樂。我不是音樂家,也不會演奏任何樂器,不過我可以盡可能去找到對他的音樂有興趣的音樂家來增加演出的機會,包括盡可能的多錄製、發行CD。Olympia魏因貝格系列的17張CD中,我擔任要角的有6張。那系列我所參與的最後一張CD是第7、8和9號弦樂四重奏,由年輕的俄國團,達米能四重奏(The Dominant Quartet)所錄製,該團是由偉大的大提琴家柏林斯基(Valentin Berlinsky)推動組成的,他也是魏因貝格的摯友。不幸的是,這也是該系列的最後一張,因為Olympia在2000年發行這張CD不久後就破產了。Olympia的唱片目錄中有那麼多傑出音樂家演奏的精彩音樂,真是非常可惜。1990年代末,波蘭指揮家許默拉(Gabriel Chmura)來找我,我幫他拿到一些Olympia魏因貝格系列的CD。他想演出的作品之一是寫於1964年的第8號交響曲「波蘭之花」,該曲是魏因貝格根據他最喜愛的詩人圖維姆(Julian Tuwim)的詩作而寫。許默拉想盡辦法引起華沙愛樂和合唱團對演出該曲的興趣,後來於2000年3月3、4兩日在華沙演出,其中第一場由波蘭廣播電台現場直播,那同時也是該曲在波蘭的首演。我太太跟我邀請安娜和奧爾嘉一起去華沙,兩場演出和彩排都聽了。我們也在華沙城裡走了很長一段路,最終找到魏因貝格被迫離開這個他摯愛的城市前居住的房子,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那都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後來許默拉持續推廣魏因貝格的音樂,在Chandos錄了三張他的管絃樂作品。魏因貝格過世後不久,我就跟佩爾說「你一定要幫他寫一本傳記」。他當然意識到這個任務的難度,但也同意了。舉例來說,魏因貝格絕大多數的樂譜都無法在俄國境外取得,因此他得窮盡一切可能的去找,西方世界只有Sikorski出版過一些(Peermusic是在幾年後才開始出版)。Sikorski還有幾首重要作品的手稿,佩爾因而得以把其中幾首借回去研究。此外,我跟史威隆也把手邊各自有的樂譜借他,那些譜不是奧爾嘉和安娜給我們的,就是向作曲家協會買來的。儘管如此,這些資料與傳記所需還相差甚遠。另一個困難點是魏因貝格跟蕭士塔高維契一樣沒有留下日記,關於自己的音樂也很少寫下或談論想法,相反的,他會說「我的日記就在我的工作、我的音樂中。」有關他作品和人生的文獻真的是令人沮喪的少。
DSCH:現在我們了解佩爾為什麼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去拼湊那些資料了!
TP:是的,佩爾在2007年一月過世前已經作了不少研究,不過這距離一般所謂完整的傳記還是差非常遠。他因為心臟問題住院時,有把所有資料燒在一張CD裡寄給我,他太太也有一份。原本的計畫是傳記完成後,由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Toccata出版社出版,因此馬丁知道佩爾的進度。後來,馬丁找上大衛.芬寧(David Fanning),詢問他是否有意願接續佩爾的寫作計畫。芬寧不僅是蕭士塔高維契音樂和蘇聯音樂的權威,一直以來也對魏因貝格的音樂有高度興趣。2008年八月,大衛到瑞典的烏普薩拉拜訪佩爾的遺孀,看過佩爾留下的資料後,決定扛下完成傳記的任務。 大衛和他的妻子蜜雪兒.雅塞伊(Michelle Assay)為完成傳記投注了大量心力。在這趟「旅程」中,我也試著幫他們作一些查證之類的工作。大衛為2010年的布雷根茲音樂節寫了一本較短的魏因貝格傳記:「米茲斯洛夫.魏因貝格:追尋自由」,我同樣提供一些協助。我很高興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心血多少有助於魏因貝格傳記的完成,該書預計將在2019年魏因貝格的百歲冥誕前出版。